1621年,乘“五月花”号移民船来到北美的“分裂派”(Separatists)清教徒们,在今天的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普利茅斯镇地区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更重要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可以不受干扰地追求自己的信仰了。清教徒们一踏上北美大陆就跪倒在地,感谢上帝引导他们穿越大洋,保佑他们平安到达。那么,上帝赐给他们的是
- 欧洲杯直播
- 2024-12-20 00:30:24
- 2
来到詹姆斯城的小女孩儿是印第安人的公主,首领波哈坦(Powhatan)的宝贝女儿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她可比她爹有名多了。1995年,迪斯尼的动画片“宝嘉康蒂”(Pocahontas),或译为“风中奇缘“,让波卡洪塔斯与约翰·史密斯的故事走进千家万户,影片主题曲“风的颜色”(Colors of the Wind)也随之广为流传。“你能否唱出山的声音,你能否绘出风的颜色?”也许正是这个简单的问题,使史密斯认识到新大陆不只是一片等待被征服的土地,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有生命和灵魂,都在印第安人的手中和心中。
波卡洪塔斯对殖民者的到来很兴奋。当波哈坦和他的部族冷眼旁观英国人的一举一动时,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经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她喜欢船上的白帆,喜欢殖民者们带来的新鲜玩意儿,甚至喜欢绅士们那身不伦不类的打扮。当她的父亲正琢磨着对这帮不速之客下重手时,她却自己跑到詹姆斯城玩儿去了。她的天真烂漫和善良友好很快就让所有的人喜欢上她。小姑娘来得越来越勤,不只是来玩,还经常给大家带吃的。人们渐渐发现,其实她真正感兴趣的人是殖民地的领袖约翰·史密斯。
也许是史密斯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劲儿,也许是史密斯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波卡洪塔斯仰慕不已。而史密斯也被为小姑娘浑然天成的气质所吸引。她就像一股清新的风,在史密斯面前展示着一个绚丽多彩、充满情感和灵性的弗吉尼亚。此时,史密斯28岁,波卡洪塔斯大约14岁。两人虽然年龄悬殊,却开始了一段异乎寻常的友谊。
史密斯认为,要想在弗吉尼亚活下去,必须跟印第安人搞好关系。在波卡洪塔斯的帮助下,他开始试着跟波哈坦接触,用从英国带来的工具和毯子换印第安人的玉米。史密斯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眼里不揉沙子,绝对不吃亏,但同时又诚实,公平,讲信用,很快就赢得印第安人的尊敬,不但为殖民地换来急需的粮食,而且学会了印第安人的捕鱼和打猎方法,甚至他们的语言。他一再向波哈坦表示,自己是为和平而来,但波哈坦很难完全相信他,因为以前西班牙人也曾骚扰这个地区,与印第安人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血的教训使波哈坦对欧洲殖民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有一次,史密斯来谈生意,却被几个波哈坦族勇士抓起来,推到波哈坦面前,准备处死他。关键时刻,波卡洪塔斯扑到史密斯身上,逼迫父亲放掉了史密斯。还有几次,波哈坦和他的手下设计好陷阱,想把殖民者们一网打尽,又是波卡洪塔斯提前报信,使他们免于灾难。这么一来二去的,再加上史密斯能说会道,波哈坦与史密斯之间从相互提防变成惺惺相惜,波哈坦族终于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了史密斯,待他如家人一般。史密斯与波卡洪塔斯的友谊以及他与波哈坦的交情为詹姆斯城殖民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与此同时,纽波特船长又从英国带来两批殖民者,到1609年9月,詹姆斯城已从最初的105人增加到约500人。
人口的增加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对土地的争夺。印第安人认为土地是大家共享的财产,人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英国人一向都是“我占的就归我”,根本不懂“公有”的概念。于是,冲突开始发生,但有史密斯压阵,基本上还算平静。1609年9月的一次火药爆炸让史密斯身受重伤,他不得不返回英国治疗。临行前,他亲自查看了仓库里的存粮,认为足以支持10个星期。根据与波哈坦的约定,印第安人将继续为殖民地提供粮食。而且,附近还有个“野猪岛”,实在不行时打几头野猪还是没问题的。
1609年10月,史密斯回到了英国,从此再也没有光顾弗吉尼亚。他后来去了由“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并把那个地区命名为“新英格兰”(New England)。他从弗吉尼亚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好几本书,包括《弗吉尼亚史》,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在书中严厉抨击了绅士们的所作所为,大声疾呼新大陆需要的是“劳动者”。他告诉大家,弗吉尼亚没有黄金,有的是无穷的机会,凡是勤奋工作的人都可以发财致富。他的书不仅让英国人对弗吉尼亚充满向往和热情,也为后来“清教徒”们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史密斯离去不久,人们就告诉波卡洪塔斯说他已经死了。波卡洪塔斯伤心欲绝,波哈坦也非常痛惜,他甚至派人去伦敦打听史密斯的情况。波哈坦只欣赏史密斯,对别人他可不买账。随着英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不断升级,波哈坦下令停止供应殖民地粮食,并封锁了詹姆斯城周围的地区,这下殖民者们连打猎都很困难了。绅士们旧病复发,史密斯前脚走,他们后脚就不干活了,还自私地霸占了大部分粮食。
1609年11月到1610年5月成了殖民地的“饥饿时代”(Starving Time),英国人从来没这么悲惨过。粮食吃完了,就吃狗,猫,老鼠,蛇,靴子,鞋,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吃。终于,在1610年5月,两艘英国移民船在詹姆斯城靠岸。此时的詹姆斯城几乎一片废墟,500名殖民者中只有60人幸存。这60个人的模样跟骷髅没什么区别,只剩下喘气的份儿了。
这两艘船本来是应该早点来的,可是途中遇上飓风,把原先的大船吹散了架。幸好飓风是在百慕大(Bermuda)附近,他们停在百慕大群岛,重新造了两条小船,才来到詹姆斯城。乘客们在海上饱受“黄热病”(Yellow Fever)的折磨,死了很多人,尸体都扔进了大西洋。但人们还是满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义无反顾地奔向弗吉尼亚。这些身心疲惫的人从船上走下来,还以为终于到了富饶美丽的新大陆,结果看到的却是一个人间地狱。你能想像他们此时的心情吗?
1610年6月7日,詹姆斯城所有的殖民者,都爬上了那两艘小船。“拜拜,弗吉尼亚!”“拜拜,新大陆!”“我们受够了!”“我们回家啦!”“再也不来啦!”两艘船离开詹姆斯城,顺河而下,出了河口就是大西洋,人们恨不得马上回到英国。就让詹姆斯城成为第二个“消失的殖民地”吧,这年头谁还顾得上它啊。
然而,他们并没有走远。6月10日,他们迎面遇上了由德拉瓦男爵(Lord de la Warr)率领的移民船。德拉瓦男爵是新任弗吉尼亚总督,带来150人,也带来了粮食和武器。他说服了这些归心似箭的殖民者们,大家一起回到詹姆斯城。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德拉瓦男爵这号人物,如果没有他的振臂一呼,殖民地的历史将会如何?160多年后,北美东部沿海的三个小县结合成为一个殖民地,派代表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后来,她又率先接受了《美国宪法》,成为加入联邦的“第一州”(The First State)。这就是用德拉瓦男爵的名字命名的“特拉华州”(Delaware)。
贵族出身的德拉瓦男爵是个铁腕领袖,也是个残暴的军人,参加过英国对爱尔兰的征服战争。他把对付爱尔兰人的政策原封不动地搬来对付印第安人,那就是烧、杀、抢。1610年8月,德拉瓦男爵派人袭击波哈坦族的一个部落,挑起了历时四年的“第一次盎格鲁-波哈坦战争”(First Anglo-Powhatan War,1610 – 1614)。在这次袭击中,他们烧毁了印第安人的房屋和玉米地,杀死七十多人,抓走部落首领的妻子和孩子。沿河返回时,他们把孩子们一个个从船上往水里扔,同时开枪射击,以把他们打得“脑浆迸裂”为乐。在詹姆斯城,他们把利剑刺进了那位首领妻子的心脏。
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波哈坦族的强烈反抗。他们虽然没有先进的武器,却凭着对地形的熟悉,用弓箭长矛和各种对付猎物的手段让殖民者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久,德拉瓦男爵因病回国,托马斯·戴尔爵士(Sir Thomas Dale)继任。他认为,若想让詹姆斯城不受威胁,必须占领周围的地区。他领人不断沿詹姆斯河修建据点,1611年5月,建成“亨利卡”(Henrico),还陆续盖起比较正规的房子,医院,仓库,和教堂。
1612年底,战争开始渐渐缓和下来,双方都精疲力尽,和平成为人们共同的愿望。1613年4月,亨利卡来了一位客人,她不是别人,正是波卡洪塔斯。但是这一次,她不是主动来的,而是被拐骗来的。戴尔以她为人质,要挟波哈坦。波哈坦见女儿被抓,便停止了对殖民地的进攻,同意和谈。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
在双方谈判的一年中,波卡洪塔斯一直住在亨利卡。她曾是殖民地的恩人,殖民者们对她倒是待如上宾,还向她宣扬基督教,教她英语。不久,波卡洪塔斯受洗成为基督徒,并有了一个英文名字“丽贝卡”(Rebecca)。当年的小姑娘此时已经十八九岁,正是豆蔻年华。有个年轻的英国商人,名叫约翰·罗夫(John Rolfe),他的种植园恰好在亨利卡附近。他很快就爱上了这位美丽的印第安人公主,并写信给戴尔总督,要求与波卡洪塔斯结婚。戴尔批准了他的请求,并率领大队人马,亲自“护送” 波卡洪塔斯回到波哈坦的驻地,与他缔结和平协议。
波卡洪塔斯与约翰·罗夫
1614年3月,和平终于降临。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庆典的最高潮正是波卡洪塔斯和约翰·罗夫的婚礼。他们的结合是英国第一桩跨种族的联姻,也是弗吉尼亚和平的重要保障。波哈坦没有参加婚礼,只派了自己的弟弟和两个儿子来。女儿离开了印第安人的世界进入英国人的社会,他也许正黯然神伤吧。
1615年初,波卡洪塔斯生下一子,罗夫成了世界上最骄傲的父亲,他要带波卡洪塔斯回英国看看。正好,弗吉尼亚公司为了宣传新大陆,也邀请他们回来做一次“公关之旅”。1616年,他们回到英国。波卡洪塔斯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征服了伦敦的社交界,成为人人追捧的“明星”,她毫无疑问是弗吉尼亚最美丽的代言人。有一次,她参加了一个特殊的化妆舞会,这个舞会的主人正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波卡洪塔斯的异域风情让这位性格阴沉、心理灰暗的国王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波卡洪塔斯惊喜地得知约翰·史密斯还活着,她热切地盼望史密斯来看她,但史密斯迟迟没有现身。当他最终出现在她面前时,史密斯似乎不习惯这个一身英国贵妇打扮的“丽贝卡女士”(Lady Rebecca),他再也看不到那个弗吉尼亚丛林中的小女孩了。两人几乎不欢而散。这次分手成了他们的永别。1617年3月,波卡洪塔斯与罗夫启程返回弗吉尼亚。船还没驶出泰晤士河,波卡洪塔斯就病倒了。她的丈夫把她抱下船,送进医院。不久,波卡洪塔斯去世,年仅22岁。她死于天花。
罗夫把波卡洪塔斯葬在她去世的小镇,把儿子暂时托付给家人抚养,满怀着悲伤,独自回到弗吉尼亚,继续打理他的种植园。可别小瞧这个种植园和它的主人,正是这位约翰·罗夫让弗吉尼亚的殖民者们找到了“黄金”。这种特殊的“黄金”长着宽宽的叶子,干了会变成金棕色,碾碎后放进小筒中可以吸。你猜对了,这就是烟草。
弗吉尼亚的自然条件很适合种烟草,但一直竞争不过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因为品种不好。约翰·罗夫冒着生命危险从西印度群岛偷来他们的品种,在弗吉尼亚培植出一种比较甜的烟草。这个新品种很快就风靡英国,贵族们以吸弗吉尼亚的烟草为“时尚”。殖民地的经济从此转亏为赢,走上繁荣富裕之路。烟草变成弗吉尼亚的“现金作物”(Cash Crop),在很多场合它也是被当作“现金”来使用的。
既然烟草就是钱,就是黄金,那人们只要拼命种烟草就是了,弗吉尼亚岂不是万事大吉了吗?可惜,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烟草是很娇贵的,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即使专业农民也没精力伺候太多。疾病,战争,饥饿,让弗吉尼亚最初的一万名殖民者中有五分之四,也就是八千人,在来到新大陆后一年之内就丧命了,所以,劳动力异常昂贵。弗吉尼亚公司在英国拼命做广告,引诱人们移民北美,奖励带“合同工”(Indentured servants)去北美的人,以至于伦敦人贩子猖獗,经常在大街上劫人,卖到新大陆。监狱里的犯人只要同意去北美,就可以获释。即便如此,仍有不少犯人宁肯呆在英国的监狱,也不愿去弗吉尼亚。80%的死亡率,这不是跟判死刑差不多吗?
对劳动力的急需使黑奴贸易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现实。奴隶贸易不是新大陆的发明,它已存在了上千年。非洲部落之间打仗的战俘就会变成奴隶,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最先开始洲际间的奴隶贸易。1619年,一艘葡萄牙船带着350名从非洲安哥拉抓来的黑人,打算把他们卖到巴西。可是途中被一艘荷兰船和一艘英国船劫持,这两只船平分了“货物”,先后来到詹姆斯城。这350个黑人立刻被“抢购”一空。当时他们还是做为“合同工”被抢购的,合同期满后很多人获得了自由。渐渐地,殖民者们发现,如果让这些黑人的合同永远不到期,那多合算。于是,奴隶和奴隶制在新大陆诞生了。
1619年,第一船女人也被运到詹姆斯城。她们都出身欧洲的穷苦人家,走投无路,被人贩子带到北美。当时,詹姆斯城的男女比例为8:1,可以想像羊入狼群的画面了吧?码头上的到处都是这样的交易:“嘿,哥们儿,想要老婆吗?”“当然!多少钱?”“120磅烟草,怎么样?”“成交!”
1619年,殖民者们终于获得在新大陆拥有土地的权利,弗吉尼亚公司总算想明白,人们九死一生图的不就是土地嘛。
1619年,第一个殖民地议会(House of Burgesses)出现了,代表们负责制定法律法规,开始了长达150多年的殖民地“自治”(Self-Government)时期。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议会和1620年“清教徒”们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新大陆未来的政治体制打下了基础。殖民地人自己管理自己,成为北美英属殖民地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它与西属殖民地最大的不同。150年后,当这个“自治”体制受到威胁时,人们将拿起武器,捍卫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利,并最终走向独立。
詹姆斯城日益繁荣,殖民者们不断扩张,不可避免地引起与印第安人的矛盾,弗吉尼亚的和平再次受到挑战。1618年,波哈坦去世,他的弟弟欧佩坎诺(Opechancanough)成为波哈坦族的领袖。他比哥哥更精明,更勇敢。他深知殖民者们一定会得寸进尺,最终将使印第安人无立足之地。1622年,欧佩坎诺策划了一次对詹姆斯城的突然袭击,杀死350个殖民者,占殖民者总数的三分之一。要不是一个成为基督徒的印第安男孩儿给殖民者们报信儿,损失会更大。这个事件被称为“大屠杀”。殖民者们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并在此后的20年里,流血不断,终于酿成“第二次盎格鲁-波哈坦战争”(Second Anglo-Powhatan War)。战争结束时,印第安人基本上丧失了对弗吉尼亚的控制权。
1622年的大屠杀使英王詹姆斯一世对弗吉尼亚公司彻底失去了耐心。自1607年以来,殖民者在新大陆的超高死亡率,使国王认为弗吉尼亚公司没有履行公司宪章(Charter)所确立的宗旨,无力保护英国人的安全。他下令解散弗吉尼亚公司,将殖民地收归“国有”。1624年,弗吉尼亚成了“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y),由国王派总督进行管理。但殖民地议会被保留下来,成为与总督府平起平坐的立法机构,“自治”仍然是殖民地的主要管理方式。
现在,我们要暂时告别弗吉尼亚了,但她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这里沉淀了太多历史的佳酿,我们只能在今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慢慢品尝了。
时间到了1621年,“清教徒”们已经在“新英格兰”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并得到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那些满怀着对宗教自由的追求而来到新大陆的人们,真的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自由的乐土吗?他们梦想中“天堂的国家”是什么样的?请看下一个故事:以上帝的名义。
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自由都没有像在美国这样得到如此透彻的理解,也没有像在美国这样被赋予如此高的价值。热爱自由是美国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点。然而,自由并不是上帝赐给美国的理所当然的礼物,也不是那位永远以胜利者的姿态高举着火焰的骄傲的女神。事实上,自由在新大陆步履艰难地走了400年,不断地变换着面孔和内容,她的每一个脚印都是血淋淋的。
1630年建立起来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让“纯净派”(Puritans)教徒们获得了自由,却让所有的非“纯净派”成员失去了自由。天主教徒,犹太教徒,英国的“新教”徒,“教友会”教徒(Quakers),“浸礼会”教徒,以及基督教的其他派别,都被视作异端,或遭鞭打,或被驱逐,或被送上绞刑架。
1631年2月,一位28岁的“纯净派”学者来到波士顿。马萨诸塞湾总督约翰·温特若普(John Winthrop)热情地欢迎了他,并邀请他担任波士顿教堂的助教。这可是个地位崇高、令人羡慕的职位,很多人做梦都想得到。但是,这个人不但拒绝了总督的邀请,还谴责了“纯净派”在马萨诸塞湾的所做所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疯了吗?这个人是谁呢?
此人名叫罗杰·威廉斯(Rodger Williams),1603年生于英国。他是个天赋极高的语言学家,精通拉丁语、希伯来语、希腊语、荷兰语、法语等9种语言。威廉斯毕业于剑桥大学,是著名的神学家。在剑桥上学时,他成为“纯净派”的一员。他不但学问出众,而且为人厚道,总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周围的人,深受人们的尊敬,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与其他“纯净派”成员一样,威廉斯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恪守“纯净派”的教条,相信《圣经》中的上帝是真正的、唯一的造物主。
从剑桥毕业后,威廉斯四处传教。他亲身感受到因信仰不同而引发的宗教战争给欧洲人带来的苦难,也目睹了英国教会的腐败与专制。渐渐地,他从研究和实践中得出了自己对宗教信仰的认识。1631年,当他到达北美时,他已经接受了很多“分裂派”的观点了。威廉斯拒绝温特若普总督的第一个理由是:“纯净派”与英国教会的决裂不够彻底,它仍然深受英国教会的影响。
接着,威廉斯阐述了自己的另外两个著名的观点。第一,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他说,信仰的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是上帝赐给每个人的礼物,是天赋人权。人们应该追随心灵的感受去选择自己的宗教,任何人都无权将信仰强加到别人身上。“强迫的信仰会让上帝觉得臭不可闻。”第二,为了保证信仰自由,教会与政府必须彻底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威廉斯认为,“基督的花园”(教会)与“野生的世界”(政府)之间应该有一道高高的“隔离墙”(Wall of Separation)。政府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教会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信仰是“个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政府只能管理世俗事务,无权干涉人们的精神信仰。反之,教会也不能介入政府的施政方针。他说,耶稣从来没有号召用“钢铁之剑”(Sword of Steel)去帮助“精神之剑”(Sword of Spirit)。
不要忘了,罗杰·威廉斯生活在十七世纪。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所有的国家都有“国教”,比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天主教,俄罗斯的东正教,英国的新教,等等;当然,所有的国家都没有宗教自由。威廉斯岂止惊世骇俗,他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指责马萨诸塞湾没有宗教自由,而且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过于密切。
温特若普总督对他的言论非常吃惊,他不明白这个本来前程似锦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邪道”。威廉斯离开波士顿,到了“分裂派”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他受到威廉·布莱德福总督的欢迎,并开始在那里传教。普利茅斯与马萨诸塞湾的信仰基本上相同,两者之间一直关系不错。虽然普利茅斯是“分裂派”的天下,但没多久,威廉斯就发现这些“分裂派”其实与“纯净派”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而且他们的专制作风如出一辙。
1633年,威廉斯离开普利茅斯,回到马萨诸塞湾的西冷镇(Salem)。西冷镇的教会比较倾向于“分裂派”,也比较宽容,为威廉斯提供了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场所。可是,接下来,不安分的威廉斯提出了他的第四个观点,立刻让马萨诸塞炸开了锅。他说,英国国王根本无权把美洲的土地分给殖民者,因为他不拥有这个大陆。国王应该先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土地,然后才能合法建立殖民地,否则,他签发的这些所谓的“公司宪章”和“土地授权书”就是一堆废纸。
这就太过分了,弄了半天,堂堂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成了“伪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1635年10月,马萨诸塞湾议会(General Court)对威廉斯进行了审判,决定将他驱逐出马萨诸塞,并准备了船,打算把他押回英国。1636年1月,当执法人员来到威廉斯家抓他时,却发现他早在三天前就溜号了。威廉斯虽然有点“二杆子”劲儿,但不傻,他可不想乖乖地等着被送回英国。当时,他正生着病,在齐膝深的大雪中,奔走105英里(大约140公里),到了那拉甘塞湾(Narragansett Bay)。住在这里的“湾帕诺”族(Wampanoags)印第安人救了他的命。他们把他带到了首领马萨索(Massasoit)的大帐。
还记得马萨索吗?他就是那位曾帮助过清教徒并与他们一起庆祝丰收的印第安人首领。我们在后文还会提到他。此时,马萨索以一贯的热诚款待了威廉斯,让他养好病,帮他安顿下来。后来,他们成了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极有语言天赋的的威廉斯,很快就可以与印第安人交流了。在接触中,他发现印第安人根本不是“低等”民族或野人,他们一点也不比英国人差。威廉斯认为,在上帝面前,他们与英国人完全平等。
1636年,在马萨索的帮助下,威廉斯从那拉甘塞湾的其他印第安部落手中购买了一块土地,与十二个支持者一起,建立起一个新的殖民地: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意思是“神意”、“天佑”。后来她与另外两个小殖民地合并成为“罗得岛殖民地”(Colony of Rhode Island),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罗得岛州。
罗杰·威廉斯是罗得岛殖民地的灵魂与支柱,他为罗得岛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1643年,当周围势力强大的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和康涅狄克殖民地联合起来,企图干掉罗得岛时,威廉斯亲赴伦敦,为罗得岛争取合法地位。当时,“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正如火如荼,“纯净派”已经控制了伦敦,马萨诸塞又派人在议会(Parliament)游说,阻止英国政府承认罗得岛。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威廉斯居然成功地取得了“宪章”,使罗得岛得到法律的保护。他的敲门砖就是自己刚出版的大作《美洲语言入门》(A Key Into the Language of America)。此书是第一本关于印第安人语言的字典,正是当时英国人急需的。它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头号“畅销书”,为威廉斯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他就是凭借着自己做为著名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力,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后,他又依靠印第安人的帮助,消除了几个大殖民地的武力威胁。威廉斯多次当选为罗得岛的“总裁”(President),在1676年的“菲利普国王的战争“中,70多岁的威廉斯被推举为罗得岛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保卫罗得岛的安全。
在罗得岛,威廉斯完全实施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主张。虽然他自己是非常虔诚的“纯净派”基督徒,但他欢迎所有不同信仰的人来罗得岛,包括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教友会”和“犹太教”教徒,甚至无神论者。威廉斯坚决反对马萨诸塞的“纯净派”强迫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的做法。尽管他与印第安人交情过命,但终其一生,他没把任何一个印第安人“教化”成基督徒。威廉斯不是第一个提出“政教分离”的人,却是第一个实践它的人。罗得岛政府依照一套民主程序管理世俗事务,绝不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在威廉斯的领导下,罗得岛成了真正的“自由乐土”。这个今天美国面积最小的州,只有四千多平方公里,一百多万人口,在地图上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美国的民主建设史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巨人。
1683年,80高龄的威廉斯去世。他的一生都在宗教与政治的漩涡中度过,被视为有“危险思想”的人物,因为他显然超越了他的时代。后来的政治家们,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构建民主政体的过程中,曾多次引用威廉斯及其他英国政论家的“隔离墙”概念。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后,美国的建国“国父”们(Founding Fathers)几乎全盘照搬了威廉斯的思想,把“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写进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也就是“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第一条(第一到第十修正案合称“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是“美式”自由与民主的基本保障,它让这个以基督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否定了基督教(以及其他一切宗教)成为“国教”的可能,避免了折磨欧洲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在新大陆重演。它不仅为新生的国家带来长治久安,也为自由提供了最广阔的发展空间。
标新立异的威廉斯并不孤独,因为还有一位比他更过分的人。此人不但激进,而且,呃,是个女人。她是威廉斯的追随者,与他一起创建了罗得岛殖民地。她的言行把马萨诸塞搅得鸡犬不宁。她的名字叫安·哈金森(Anne Hutchinson)。
安·哈金森原姓马尔贝瑞(Marbury),生于1591年。1612年,她与威廉·哈金森结婚。夫妇俩都是“纯净派”教徒,于1634年来到马萨诸塞湾。与那个时代所有的女人一样,安·哈金森不住脚地生了14个孩子。与其他女人不一样的是,她还有自己的脑子,会独立思考。她精力过人,思维敏捷,口才极好,十个男人也说不过她。
在十七世纪,女人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妻子从家中逃走,那她就是个盗贼,不仅“偷”走了自己,还“偷”走了她身上的衣服。既然女人是“财产”,她们在公共场合就绝对应该“噤声”。你见过谁家的桌子板凳说话吗?
可以想像,当安·哈金森开始在大厅广众演讲时,那是怎样一个轰动效应。温特若普总督简直气疯了,他就纳闷儿,家里有14个等着吃饭的孩子,怎么还不够这个女人忙活的,她哪来的闲功夫在这儿妖言惑众呢?不仅如此,她还在家中组织“查经班”(Bible Study),与大家一起探讨《圣经》的原意,得出的结论与“纯净派”的“官方”解释大相径庭。更糟糕的是,不光女人听她讲,后来连男人也来听,她的“查经班”很快就发展到80多人,家里盛不下,只好挪到附近的教堂去讲。再后来,她搞的这一摊子竟然成了气候,被称为“哈金森运动”(Hutchinsonian Movement),从者如云。
安·哈金森象威廉斯一样,提倡宗教自由。她对《圣经》进行了非常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对很多教条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她挑战“纯净派”教会的权威,认为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有罪,她们在教会中应该享有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应该不受限制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她说,做女人是“上帝的恩赐”而不是“上帝的诅咒”。哈金森声称自己拥有“来自上帝的灵感”,可以辨别“上帝的选民”。对十七世纪的人来说,她实在是太前卫了,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承受力。本来,由于家庭的渊源,很多“纯净派”领袖,如温特若普总督,约翰·科顿等人,都是她的朋友。可她实在太“离谱”,这些昔日的朋友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
1638年,马萨诸塞议会开始审判哈金森。当时,46岁的她正怀着第15个孩子,可是他们却强迫她站着受审好几天,导致了她的最后流产。在审判中,哈金森为自己做辩护。如果你看一下当时的记录,就会发现,安·哈金森的智商比那些审判她的人高多了。她的辩护有理有据,清晰的逻辑,雄辩的技巧,使律师出身的温特若普总督都捉衿见肘,更不用说别人了。当然,不管哈金森说什么,结论早在开审之前就做好了:她被驱逐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
安·哈金森和她的丈夫率领追随者们来到罗得岛地区,与威廉斯一起建立了后来的罗得岛殖民地。1643年,在丈夫去世后,安·哈金森决定举家迁往现在的纽约市地区。当时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正与荷兰人打得不可开交。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印第安人闯进她的家,杀死了她和所有随她来纽约的家庭成员,只有红头发的小女儿幸免于难。这个不幸事件成了马萨诸塞湾“纯净派”的口实,温特若普总督说:“这是上帝的惩罚。”
1922年,马萨诸塞州政府把安·哈金森的雕像纪念碑安放在州府大楼前。碑座上写着:“安·哈金森……公民权利与宗教自由的勇敢的倡导者。”不能见容于她的时代的哈金森,在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许,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并为它奉献了一切。安·哈金森的伟大其实很简单:她敢于思考。
安·哈金森虽然死了,但她开启的“哈金森运动”却没有终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想了。温特若普总督真够倒霉的,摁下葫芦起来瓢,好不容易打法走了一个哈金森,又出了个比哈金森更让他头痛的女人。她比哈金森更麻烦,而且,她不要命。
这个女人就是玛丽·戴耶(Mary Dyer),1611年生于英国。她原姓巴利(Barrett),1633年与威廉·戴耶(William Dyer)结婚后,来到波士顿。她丈夫威廉是温特若普总督的朋友,当他把玛丽介绍给总督时,温特若普赞美说:“真是位庄重优雅的女性。”可是,没多久,温特若普就会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这位“优雅的女性”变成了他的噩梦。
1637年,玛丽公开支持安·哈金森。1638年,她和丈夫被赶出马萨诸塞,跟着哈金森去了罗得岛。1652年,当威廉斯第二次去伦敦为罗得岛办事时,玛丽和丈夫一同前往。在伦敦,她变成了一个“教友会”信徒(Quakers)。
什么是“教友会”?像“纯净派”一样,它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自称为“朋友宗教协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简称“教友会”,或“公谊会”。听上去有点像黑社会吧?在十七世纪的人们心中,它就是黑社会。人们厌恶地称它为“Quakers”,音译为“贵格会”,意译为大麻烦。
“教友会”最主要的观点是:人们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不用依靠教会或教士。每个人都通过心灵感应与上帝交流,并接受上帝的旨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高低尊卑之分,大家都是朋友。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思考,不同意见之间互相宽容。他们没有“礼拜”或“布道会”,也不是大家坐在那听教士讲。他们的聚会叫“开会”(Meeting),男女老幼坐在一起,谁觉得自己受到了上帝的启发,就站起来讲两句,跟讨论会似的。他们只拜上帝,不拜国王,更不相信教会的权威。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教友会”这么招人恨了吧?它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你直接跟上帝聊天,那还要教会干什么,要教士干什么?你都能接受上帝的旨意,那“君权神授”往哪搁?男人和女人坐在一起开会,成何体统?女人她配吗?你们都学会独立思考了,谁听国王的?谁听教会的?这不是要乱套吗?人人平等?那是个什么东西?
“教友会”在旧大陆被视为罪恶,在新大陆被视为异端,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马萨诸塞先是见一个,用鞭子抽一个,后来又通过法律,把“教友会”定为非法。可玛丽·戴耶就觉得“教友会”的主张特别对胃口,跟她的追求完全一致。她一旦认定了这个理儿,那是十八头牛都拉不回来,见了棺材都不带落泪的。
1657年,玛丽回到波士顿,立刻公开抗议严禁“教友会”的法律。她被逮起来,赶出殖民地。随后,她又返回“新英格兰”传教,1658年在康涅狄克被捕。获释后,她竟然跑回波士顿看两个“教友会”的朋友。这两位早就被抓起来了,她也被抓,并被“永久性”地驱逐出马萨诸塞。可这“驱逐令”对玛丽来说就是一张废纸,她第三次返回马萨诸塞,与其他教徒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挑战殖民地的法律。这次,她不但被抓,还被判处死刑。她丈夫只好向温特若普总督求情。玛丽与其他两位“教友会”教徒同赴刑场,亲眼看着这两个教徒被吊死。就在她准备就刑的最后一分钟,行刑人把她架上马背,强行送往罗得岛。这是温特若普总督看在朋友份上最后一次救她了。
1660年,玛丽·戴耶被她的信仰第四次带到马萨诸塞,公然反抗对“教友会”的禁令。这就有点找死了。5月31日,她再次被判处绞刑。“纯净派”说只要她保证不再回马萨诸塞,他们就可以给她一条生路。她的丈夫和亲友也哀求她认罪忏悔,但她拒绝了。6月1日,玛丽·戴耶被吊死在波士顿,她终于成了殉道者。这一天,整个马萨诸塞的人都来看她就刑。这一天,是新大陆让自由蒙羞的一页。
玛丽·戴耶的死在人们心中引起很大的震动,不少“纯净派”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殖民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衡量整个事件。1661年,对“教友会”的禁律终于被修改了,玛丽·戴耶用生命为自己的信仰赢得了尊严。今天,她的雕像与安·哈金森的一起立在马萨诸塞州府大楼前供人们瞻仰,也时刻提醒人们不要让同样的悲剧重演。
“新英格兰”的殖民地在专制与自由的对抗中一天天成长。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纯净派”是一伙非常固执又非常野心勃勃的人。他们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抢地盘的时候当然也多多益善。那么,这个地区又出现了哪些新殖民地呢?印第安人对英国人的扩张将做何反应?“新英格兰”的和平还能维持多久?请看下一个故事:菲利普国王的战争。
马萨诸塞湾的“纯净派”实在有点太霸道,跟他们信仰不同的,他们容不下。跟他们信仰相同,政见不同的,他们也容不下。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建立的普罗维登斯殖民地(后来发展成罗得岛殖民地),为其他人做了个榜样。那些在马萨诸塞湾呆不下去的人,开始策划建立自己的地盘。
对马萨诸塞不满的人中,有一位叫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他是个虔诚的“纯净派”教徒,曾获剑桥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那里当了几年神学教授。在英国时,他就是个很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是非常出色的演说家,而且是个文笔犀利、见识超群的政论家。
谁也说不清楚胡克跟马萨诸塞湾的领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反正都瞧对方不顺眼。1636年,胡克一怒之下,带领100个支持者离开马萨诸塞,来到康涅狄克河谷(Connecticut River Valley),在哈特福德地区(Hartford)建立起“康涅狄克殖民地”(Connecticut Colony),后来,又与其他两个小殖民地合并,地盘不断扩大,形成了现在美国的康涅狄克州。
今天的康涅狄克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她是富豪云集之地,也是度假天堂。凡是去过康涅狄克的人,都会折服于她惊人的美丽。舒展、安详、清澈的康涅狄克河,穿过新英格兰茂密的森林。春天的芬芳,夏天的清幽,足以让人忘记今夕何夕。秋天多彩的树叶把河水染得五颜六色,连天空都变成一幅绚丽的油画。康涅狄克的海滨不但水产丰富,更有一种地老天荒之美。难怪胡克一见到康涅狄克,就认为自己到了天堂,再也不想离开半步。
美不胜收的康涅狄克河谷是新英格兰最肥沃的土地,她很快就成了整个新英格兰的粮仓。人们从拥挤的马萨诸塞涌向富饶的康涅狄克,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梦幻家园。可是,有一个问题。当初胡克带人“入住”康涅狄克时,完全是自作主张,没经过英王的批准,属于“非法”搬迁。现在虽然木已成舟,但那份文件还是不可少的。谁都知道,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对“纯净派”恨之入骨,康涅狄克的“纯净派”怎样才能获得这一纸许可证呢?
胡克家族虽然在康涅狄克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他本人并没有担任总督,而是专注于教会的事务。康涅狄克的投资人为殖民地选择了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就是马萨诸塞湾总督的儿子,小约翰·温特若普(John Winthrop II)。小温特若普是老温特若普的长子,聪明,能干,有学问。父亲移民北美后,他先是在英国照料生意,处理家族事务,后来又在马萨诸塞给老爹当助手。
做为康涅狄克的总督,小温特若普的首要任务是为殖民地取得合法地位。他收拾行装,来到伦敦。在晋见国王时,他拿着家传的宝物,那是查理二世的祖母曾戴过的戒指。小温特若普把这枚戒指奉献给国王,查理二世龙颜大悦。小温特若普施展高超的外交手段,让国王批准了康涅狄克的宪章。这个宪章的条款比其他所有殖民地的条款都宽松,给了康涅狄克极大的自主权,她的土地范围竟然延伸到太平洋沿岸,当然,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太平洋到底有多远。
1639年,托马斯·胡克帮助起草了康涅狄克的一份重要的文件,叫《基本秩序》(Fundamental Orders)。《基本秩序》是新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它的理念和结构对以后美国各州的宪法以及《美国宪法》都有深远的影响。这部宪法把康涅狄克变成最民主的英属殖民地,开始了“美式”民主制度在新大陆的“定点实验”。今天,康涅狄克州的别号之一就是“宪法之州”(Constitution State)。
就在“纯净派“在康涅狄克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英王把马萨诸塞湾北面的一大片土地赐给了自己的两个好朋友:约翰·梅森(John Mason)和弗迪南努·高吉斯(Ferdinano Gorges)。他们俩把那片土地一分为二,高吉斯得的那一块成了今天的缅因州(Maine),梅森得的那一块就是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开始时,两块地都属于马萨诸塞湾。后来,新罕布什尔变成独立的殖民地,又被英王收回,成为“皇家殖民地”(Royal Colony)。而缅因则一直是马萨诸塞的一部分,直到1820年才分离出去,成为加入美国的第23个州。
至此,“新英格兰”所有的殖民地都凑齐了。她们是:普利茅斯,马萨诸塞湾,罗得岛,康涅狄克,新罕布什尔。地广人稀的北美大陆,让来自狭隘的欧洲岛国的英国人眼界大开。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富足之地”(Land of Plenty)。她那摄人魂魄的美丽和得天独厚的物产,让英国人的贪婪之心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不息。在英国,由于地域狭小,只有贵族或大富之人才可能拥有土地,平民连做梦都没想过。可是,当殖民者来到北美,满眼看到的就是土地,似乎永远到不了尽头的土地。忽然间,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土地了,而且要多少有多少,超出了人们最疯狂的想象。面对无垠的大陆,殖民者们只有一个念头: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可他们忘了,美洲不是一片没有主人的荒野,印第安人已经在这里世代相传了几千年。他们又怎能容忍殖民者们毫无节制的扩张呢?
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主要是“湾帕诺族”(Wampanoags)和“那拉甘塞族”(Narragansetts)。跟弗吉尼亚的“波哈坦族”(Powhatans)比起来,他们的势力比较弱,也比较和平,从不惹是生非。1621年3月,清教徒在北美落脚才几个月,“湾帕诺族”的首领马萨索(Massasoit)就与普利茅斯的第一任总督约翰·卡沃(John Carver)签订了和平协议。如果没有马萨索和斯冠徒(Squanto)的帮助,饥寒交迫的清教徒们早就死翘翘了,哪里还有普利茅斯殖民地。
清教徒们倒是也知恩图报,在此后的50多年里,普利茅斯与马萨索的部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你来我往,互通有无。有一次,马萨索病得好像都快死了,普利茅斯专门派人送来药材和鹅肉煮的汤,马萨索吃后大有好转,终于康复。每当殖民地有人来拜访马萨索,他都热情地留他们在自己的大帐过夜,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与罗得岛的罗杰·威廉斯也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马萨诸塞与湾帕诺族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但他们刚开始时基本上能和睦相处。那时,很多殖民者与印第安人比邻而居。殖民者们从旧大陆带来很多家禽、家畜,比如猪,羊,牛,马,鸡,还有狗和猫。这都是新大陆没有的新鲜玩意儿,印第安人觉得很有趣。也许是新大陆的水土太有营养了,这些动物来到北美后,个个变得高大健壮起来,长得比在旧大陆时快多了。很多时候,殖民者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羊啊鸡啊就跑到印第安人的地里把人家的菜给啃了,为此闹了不少乱子。殖民地政府还专门下令让各家管好自己的牲畜,不要搔扰印第安人。
马萨索很愿意用印第安人的皮毛制品和粮食换殖民者的工具、武器和马匹。说起来很有意思,印第安人的文明不能说不灿烂,印第安人的头脑不能说不聪明。可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轮子。他们只把小轮子装在孩子的玩具上,却从未造出过任何形式的车辆。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所有的东西都靠肩挑手提头顶,非常不开窍。后来,人们似乎明白了,这是因为美洲不产会拉车的动物,如马,牛,驴,等等。没有马,要马车干什么?当殖民者把马引进美洲,印第安人立刻如虎添翼,原来他们是天生的骑手。欧亚那些又瘦又矮的马到了美洲后就像吃了化肥,全变成高头大马,衬着印第安人在马背上矫健的身影,别提多威风了。
经过多年的交易,印第安人越来越习惯用殖民者带来的武器打猎,也越来越依赖与殖民者的贸易。可是,随着殖民者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占的地方不断扩大,自然侵犯了印第安人的领地。印第安人被逼得步步后退,他们可以拿得出手的交易物品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以出卖土地为代价。
更过分的是,马萨诸塞湾的“纯净派”强迫印第安人信奉基督教。“纯净派”都是些一条路走到黑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就是把所有的人“教化”成基督徒。印第安人有自己的信仰,但他们对信仰的态度似乎不像“纯净派”那么严肃,很多人觉得多信一个上帝也没什么坏处。于是,看上去很多印第安人都归依了基督教,但大多数是白天拜耶和华,晚上拜自己的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纯净派”逼迫得越来越紧,印第安人对基督教那最初的好奇渐渐变成了仇恨。
在马萨索还活着的时候,冲突已经开始发生。马萨索尽全力周旋,勉强维持着脆弱的和平,因为他知道印第安人需要殖民者的商品。可是,其他部落成员,特别是他的儿子们,就不以为然了。马萨索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湾苏塔(Wamsutta),小的叫麦塔康(Metacom)。他们小时候,马萨索请普利茅斯的议会为两个儿子取英国名字,于是议会把古希腊两个国王的名字送给了这哥俩。老大叫亚历山大(Alexander),老二叫菲利普(Philip)。
1661年,马萨索去世,亚历山大成为湾帕诺族的领袖。1662年,他去普利茅斯与总督约西亚·温斯路(Josiah Winslow)谈和平协议的事,在回来的路上突然死亡。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在普利茅斯受到非人的虐待,被折磨而死。菲利普继承了首领之位,他公开表示了对普利茅斯殖民者的不信任。他认为是殖民者杀死了自己的哥哥,他要复仇。
菲利普开始联络其他的印第安部落,想劝说他们与自己携手合作,共同对敌。可是,印第安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团结。他们各自为政,从来没有联合的历史。这也不能怪他们。虽然他们都被叫做“印第安人”,但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时期迁来美洲大陆的,既不同种,也不同文。在美洲的印第安人说300多种不同的语言,光新英格兰地区就有7种以上。部落之间相互沟通都有困难,更不用说联合了。
菲利普还没做好准备,战争就突然爆发了,它的起因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有个叫约翰·萨塞蒙(John Sassamon)的印第安人,他是基督徒,毕业于哈佛,是普利茅斯殖民者的朋友,也是菲利普的顾问。1675年5月,他跑到普利茅斯告密说,菲利普要袭击殖民地。还没等搞清事情的真假,萨塞蒙就被人杀了。据说是印第安人痛恨他的背叛而干掉了他,但没有多少真凭实据。普利茅斯根据一个证人的证词,逮捕了三个湾帕诺族成员,其中包括一位菲利普的高级参谋。法院匆匆忙忙地进行了审判。6月8日,三人在普利茅斯被处死。菲利普认为这是对自己部族的极大侮辱,印第安人群情激愤。6月20日,湾帕诺族的一支人马,有可能是在菲利普不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了普利茅斯的一个村庄。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迅速做出反应,6月28日就派军队灭掉了湾帕诺族的一个小镇。历时两年的“菲利普国王的战争”(King Philip’s War)就这样开始了。
起初,菲利普的队伍占了上风。他们的特点是,突然袭击,来去如风,让殖民者防不胜防。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康涅狄克,罗得岛等都遭到袭击,损失惨重。但印第安人不擅久战,他们没有多少存粮,很多人惦记着回去种地打猎,很容易对战争失去耐心。他们又分成两个阵营,大部分帮着菲利普,但也有不少站到了殖民者一边。而殖民地利用海运的优势,源源不断地从西印度群岛等地购买粮食,武器也先进得多。所有的新英格兰殖民地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渐渐扭转了局面。
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卷了进去,双方都杀红了眼。殖民者们见了印第安人就砍,连保持中立的那拉甘塞族都被血洗。印第安人也杀晕了,把平时与他们非常友好的威廉斯建立的普罗维登斯城烧成一片焦土。战争虽然只持续了两年,但它的惨烈程度超过了弗吉尼亚的“盎格鲁-波哈坦战争”。八万殖民者,一万多印第安人被牵扯进来,半数以上的殖民者村庄遭到袭击,600个殖民者和3000个印第安人丢掉了性命。
随着印第安人陷入困境,菲利普渐渐失去了支持,他想争取法国援助的愿望也落空了。1676年8月12日,菲利普被部下所杀。他的头颅被砍下来送到普利茅斯,在那里“示众”了20年。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卖到百慕大为奴。印第安人对殖民者最大规模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菲利普国王的战争”使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遭遇灭顶之灾,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被迫逃离家园,向西迁入阿巴拉契亚山,或向南进入纽约、新泽西地区。除了战死的人以外,双方军队在接触中迅速传播着疾病,特别是天花。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近乎灭绝,这个地区变成白人的天下。
在整个战争中,英国国王没出一兵一卒,没花一分钱,也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战争需要的粮草和武器完全由殖民地自己筹措,军队由殖民地的志愿者组成。它让殖民者们负债十万英镑,对当时工作一年才挣二十五英镑的人们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各殖民地被战争拖得半死不活,给英国王室创造了机会。战前,英王几乎从没正眼瞧过新英格兰,任其自生自灭,可殖民者们表现出来的极强的战斗力和新英格兰日益彰显的巨大经济利益,吸引了英王的眼球。1684年,查理二世收回了马萨诸塞湾的宪章,把她变成“皇家殖民地”。1690年,普利茅斯的宪章到期,英王拒绝续约,把普利茅斯强行并入马萨诸塞,这个新英格兰最早的殖民地失去了独立存在的资格,成为马萨诸塞湾的一部分。康涅狄克因受宪章保护得以生存。罗得岛也受宪章保护,而且是与马萨诸塞信仰不同的“自由之地”,被英王故意保留下来跟“纯净派”作对。与此同时,第一个英国“新教”教会在马萨诸塞湾建立起来,从此打破了“纯净派”信仰对新英格兰的绝对垄断。
可是,英国国王的如意算盘也有不如意的时候。他战时袖手旁观,战后渔翁得利,引起殖民者们极大的不满。新英格兰,特别是马萨诸塞,与英国王室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为“美国革命”埋下了种子。在战争中,各个殖民地第一次摒弃前嫌,联起手来,一致对外。他们不仅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而且模模糊糊地开始有了一种自我意识,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也似乎觉得自己与纯粹的“英国人”不完全相同。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洗礼中,这种自我意识和凝聚力越来越强烈,一个新的民族和她那勇猛好斗的性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当然,这个从血与火中走出来的民族绝对不是善茬,从来不是。
新英格兰尘埃落定,我们可以随着英国王室,暂时把眼光转向新英格兰南面的“中大西洋“地区。英王想把弗吉尼亚与新英格兰殖民地连接起来,中大西洋地区就是必经之路。可一看才发现,这里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了。迟到的英国人能咽得下已到嘴边的口水吗?他们将如何满足自己的贪婪?英国在北美的扩张又将延伸到何处?请看下一个故事:纽约,纽约。
在我们继续讲美国的故事前,不得不先聊聊英国。英美血肉相连,要说清北美的事儿,不可能撇开英国。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北美殖民地还是初生的婴儿,她的母亲英国却风华正茂。此时,这位母亲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不仅影响着自己的孩子,还将改变世界。
自1625年查理一世(Charles I)即位以来,他与议会(Parliament)和“纯净派”(Puritans)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糟糕。他特别相信“君权神授”(Divine Right of Kings),认为只有上帝在他之上,什么法律、议会根本无权限制他的权力。这已经违背了1215年《大宪章》(Magna Carta)的宗旨。他与法国公主的婚姻使自己一步步靠近天主教,引起英国“新教”和“纯净派”的极大不安。与西班牙多年的宗教战争让国王入不敷出,议会又拒绝给国王征税的权力。于是,两者之间从唇枪舌剑闹到你死我活,终于爆发了1642到1651年的“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
虽然很多“纯净派”已经被查理一世赶到北美去了,但他们在英国的势力还是很大。此时,“纯净派”成员已经成了议会的中坚力量,战无不胜的议会将军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就是个虔诚的“纯净派”教徒。查理一世的“保王党”被叫做“骑士”(Cavaliers),因为国王的军队大多是骑兵。以“纯净派”为骨干的“议会军”被叫做“圆脑袋”(Roundheads),因为当时的男人一般都留披肩长发,可“纯净派”男教徒都是短发,他们理发时,把个大碗扣在脑袋上,然后沿着碗边儿剪头发,所以,每个人的发型都一样,个个看上去脑袋都是圆圆的。
结果,“圆脑袋”战胜了“骑士”,查理一世成了阶下囚。议会对国王进行了审判,这可是破天荒的事。以前,英国国王被废黜过,被杀过,但从未被审判过。查理一世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审判自己,那些“圆脑袋”竟然也敢人模狗样地坐在那儿当陪审团,他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啥德性。
国王拒绝认罪,拒绝妥协。在克伦威尔的主持下,议会宣布了查理一世的罪状,说他为了一己之私与人民为敌,损害了公共利益,破坏了国家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内战期间,八万五千人被杀,还有十万人死于战争传播的疾病。查理一世被定为杀人犯和“叛国者”(他曾借助苏格兰军队为自己打仗)。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他的遗言是:人民的自由来自政府,但人民绝不能分享政府的权力。
国王没脑袋了,国家总得有首脑吧?于是,克伦威尔为成了英格兰共和国(Commonwealth of England)的领袖。英国人还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没想到这帮“圆脑袋”比国王还差劲。他们强迫人们接受“纯净派”的信仰,破坏“新教”教堂,打碎宗教人物的雕像,烧毁艺术品。“纯净派”永远都认为自己是按上帝的旨意办事,所以永远正确。
“纯净派”还颁布了“禁酒令”,并关闭伦敦所有的剧院,因为他们认为娱乐是不道德的。本来,英国是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国家。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英国的戏剧就是自由言论的载体。在大街上骂娘有可能犯法,但在舞台上嬉笑怒骂却是悉听尊便,连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这么专制的君主都没限制过这种自由。正是英王对言论的宽容成就了莎士比亚的辉煌。可“纯净派”最不喜欢的就是言论自由,盎格鲁民族的幽默感到他们这儿就算失传了。莎士比亚有一部喜剧叫“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里面有一位小丑式的人物托比爵士,他在戏中拿“纯净派”开涮道:“因为你道德高尚,我们就不能吃蛋糕喝啤酒了吗?”得,就冲这,“纯净派”封杀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没把莎翁从坟墓里拉出来砍头就算不错了。事到如今,英国人才恍然大悟,唉,还是有国王的时候好啊。
【 点评:强迫人民接受信仰,实行思想专制,是最坏的政府。】
后来,克伦威尔自封终身“护国主”(Protector),解散议会,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好不容易到了1658年,总算把克伦威尔给熬死了。他儿子继位当了几天“护国主”,很快就被赶下台。人们已经受够了“纯净派”,都盼着回到吃蛋糕喝啤酒的日子。1660年5月,议会隆重请回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做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终于复辟了。查理二世性格阳光,一向被称为“快乐的君王”(Merry Monarch)。这位快乐君王可没心情让别人快乐,他把克伦威尔开棺戮尸,大肆屠杀“纯净派”。这下轮到“圆脑袋”倒霉了,他们忙不迭地逃出英国。查理二世的专制比他爹差不了多少,议会也傻眼了,这可咋办呢?后悔药一时半刻又找不着,还是先忍着吧。
“英国内战”看上去像是白忙活了,王室去而复返。但实际上,这场战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的结果,它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民是可以颠覆政府的,如果这个政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战争带来的革命理念成为后来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前奏,也潜移默化地在北美殖民者心中播下了自由、平等和革命的种子。
在“英国内战”期间,北美的殖民地分成两派。弗吉尼亚坚决站在王室一边,大骂“纯净派”,很多王室成员逃到弗吉尼亚避难。此后,弗吉尼亚一直是英王最喜欢的殖民地,因为她的忠诚,也因为她的富有。英王最不喜欢的殖民地是哪个,估计你用膝盖都想得出来,当然是马萨诸塞啦。“圆脑袋”在英国的胜利让马萨诸塞的“纯净派”(也是圆脑袋)欢心鼓舞,他们宣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后来,国王复辟,对“纯净派”大开杀戒,英国的“圆脑袋”们纷纷逃到北美。马萨诸塞当仁不让,明目张胆地窝藏钦犯,英王能不恨吗?“菲利普国王的战争”后,英王趁机把马萨诸塞好好修理了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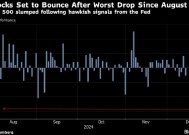











有话要说...